|
一到冬天,满大街都飘动着麻辣烫的味道,如果再下点雪,冷飕飕地钻进街头麻辣烫的小馆里,来上一碗满含酱香的麻辣烫,就会突然发现,潦草的人生仿佛又充满了意义。
其实,即使不是冬天,一年四季,沿街的麻辣烫都旗帜招展地宣示着他们的势力版图。若干年来,麻辣烫们就像河边野蛮生长的荒草,以它们原始而简单粗暴的方式收割着城乡人的胃,所到之处,几乎全域性的罕有对手。 
麻辣香锅。摄影/陈仓识火,来源/图虫创意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吃食,其貌不扬,甚至略带寒酸。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说菜不是菜,说汤不是汤,长相飘忽而荒诞的食物,不讲武德,凭着一股子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江湖打法,硬生生被以杨国福、张亮、马路边边为首的麻辣制造者烫出了一片辽阔的水煮江山,甚至,还烫出了一个美食江湖的神话,一种现象。
在这场麻辣烫对传统美食江湖的颠覆性运动的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玄机?又潜藏着怎样的社会学语法? 当麻辣烫遇上东北人
尽管麻辣烫的出生地不在东北,但麻辣烫的水煮江山却是由东北大哥打造的。
饮食的江湖几乎都有这样一个极其奇妙的现象,一道吃食的火爆基本都不是由本乡人开创的。譬如满大街的牛肉拉面,虽然都挂着“中国兰州”的字样,但大多都是在青海人手里飞黄腾达的。在全国各处飘荡的拉面,和兰州的牛肉面基本不是一个事物;还比如满大街的成都美食,虽然也都挂着“成都”的招牌,但都是由重庆人缔造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在饮食的江湖上不胜枚举。
按照麻辣烫的出生档案,它和重庆火锅的生成原理基本是一样的,都是在西南地区长江的水岸边由当地的渔民和纤夫们发明的。可以这样说,火锅就是重庆长江码头边的麻辣烫,而麻辣烫就是水边的小火锅。 
乐山麻辣烫。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段
当年,四川乐山的纤夫们,光着屁股、倾斜着身子,在江边拉纤。工作劳累,日子清苦,这个工种又匆忙劳碌,没有足够的时间像野炊似的悠闲地坐在水边享受美食。饥饿难耐之时,一伙子人凑上来,架起一口锅子,寻些草木生火烧水。因地制宜地弄些食物,鱼虾、虫子、水草等,只要能入口的,一概拿来煮了。味道不够,加上辣椒和花椒来凑,热火朝天地吃着热乎。各类杂食可以果腹,而花椒和辣椒又能祛除身上的湿寒气,关键吃着还很痛快舒服。于是,这个杂乱无章的吃食就这样广泛地流传开来。
当这个又麻又辣的食物遇上东北人,注定就要上演一段传奇。
常言道:广东人什么都可以拿来煲,东北人啥都可以拿来烤,所以,在追求美好饮食生活方面,千万不要怀疑东北人民神奇的创造力,连面筋这么奇特的东西东北人都能拿来烤了,还有什么不能造的? 
东北烧烤。摄影/抹茶不甜,来源/图虫创意
其实,东北人在吃食方面的创造力不仅体现在烧烤上,更体现在东北的乱炖上,白肉都可以拿来炖了酸菜,血肠也可以拿来煮,炖个来自四川的麻辣烫还不是小菜一碟?
东北人有乱炖的天性,有炖煮的传承基因。其实,究其本质,当年闯关东淘金的汉子们和当年在水边拉纤的纤夫们的生活水准基本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纤夫们将所有的物什都能拿来麻辣烫了,东北的汉子们将所有的物什一起拿来炖了。所以,当两个相同性质的吃食在现代东北人手上相遇的时候,一下子焕发出新世界的魔力。 
猪肉酸菜炖血肠。摄影/陈锋尘,来源/图虫创意
于是,新版本的麻辣烫在东北人神奇的创新下,就像大东北的洗浴一样,在繁乱的都市里荡起了涟漪。 万物皆可麻辣烫
这一锅的麻辣烫,就像天下的河山一样,包罗万象,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拿来烫的。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麻辣烫锅底就像一个公共广场,不管是荤的还是素的,不管是腥的还是臊的、膻的,各种食材不分职务高低,身份贵贱,个头长短,都会齐刷刷被平等地按进火热的浓汤里接受汤色的洗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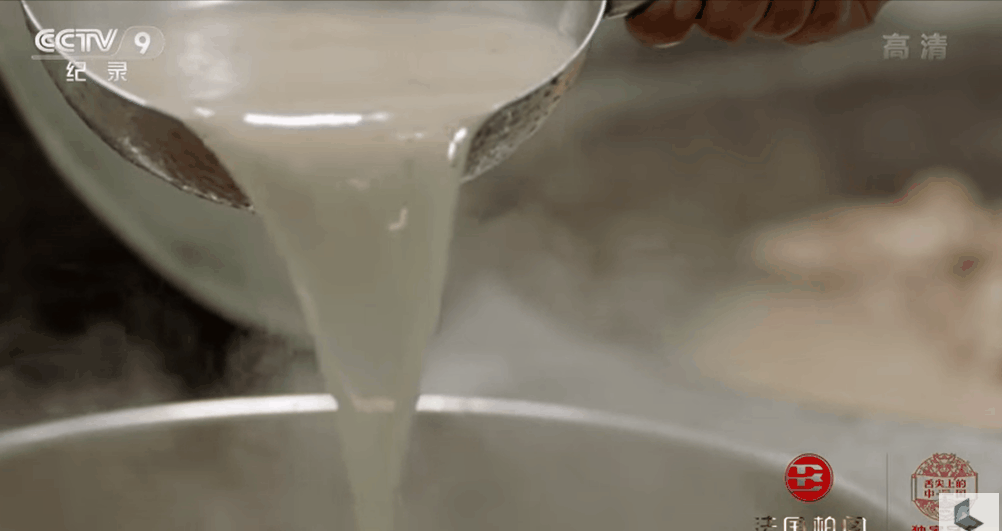
麻辣烫底汤很清淡,用炒制后的底料与高汤混合。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段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里蹦的,圈着养的,野地里自然生长的,河边爬的,挂在树枝之上的,凡是可以入口的,不管是绿的,还是红的,也不管是白的,还是黄的,大家相互拥挤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水煮世界。
每一种食物都有它天然的味性,每一种食材又有它天生的性格。有的倔强,有的温暖,有的孤傲,有的和善,有的味酸,有的味甜。而当各种食材相聚在一起,南来的白菜,北往的过客,经过不断的浸泡煮制,大家相濡以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保持自己独立个性的同时,也吸收了各种味道的精华。恰恰就是经过这么一深入的洗礼,就把这个麻辣烫弄出了人间无限的烟火气来。 
麻辣烫选菜柜。摄影/爱艺术的痞子王,来源/图虫创意
这个烟火气,就是麻辣烫的灵魂,这个烟火气,也正是麻辣烫得以在大江南北通行无阻的利器。
当麻辣烫带着诱人的芳香从河边走到岸上,当它们带着山野原始的羞涩和朴素从乡间走进城乡,通过四川人民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又泛化出各种色彩纷呈的“烫二代”出来——串串香、签签香、钵钵鸡都是这“烫二代”中的佼佼者。 
串串。摄影/仙人板板,来源/图虫创意
相较于被东北大哥拿去做了改版的麻辣烫,串串香和钵钵鸡坚强地保留了民间川味的属性和气节,坚守住了川菜的阵地和尊严。不管走到哪里,在它们身上,都鲜明地携带着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正宗味道血统。
与传统地摊的麻辣烫相比,串串香和钵钵鸡在进城时,都被事先进行了一场精心修饰和美妆升级。以钵钵鸡为例,之所以叫鸡,它清晰表明了底汤的成色——汤底一定要是鸡汤才行。同时,冠之以钵钵二字,又反映出它的出品器型和品相的优雅美观,尽管是金属的钵字,但它并不是敲锣打鼓的铙钹,也不是苦行僧们化斋的衣钵,而是陶瓷的钵。 
钵钵鸡。摄影/爱摄影的兰兰,来源/图虫创意
经过一番收拾打扮,麻辣烫已经出落得犹如村里的小芳姑娘一样,既保留了乡间的纯朴,又多了一份城市的现代时尚气息。不管她是归属于凉菜,还是归属于热菜,都以她缭绕的芳香呼唤着都市青年一族的味蕾。
尽管麻辣烫在美食江湖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它又略带一种遗憾,甚至是缺陷。虽然它色香诱人,汤底浓厚,但这锅底汤大抵却是不能拿来喝的。这就给关东煮的流行留下一个可以生长的空白。
顾名思义,关东煮来自于日本的关东地区,虽然它也是水煮的吃食品种,但它和麻辣烫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底色:关东煮的最大特点是,在它这里不但可以吃上水煮的肉丸和萝卜,关键这口盛在杯子里的汤汁,和日本的面汤一样,都讲究一个醇厚而鲜美,如果能被食客们一饮而尽,那才算是真正的好汤。 
关东煮。摄影/xiaosan,来源/图虫创意
关东煮早期依托着便利店进入中国美食江湖,随着24小时便利店广泛的布局店,加之超市和餐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于是,关东煮也开始在都市上班一族中流行开来。 麻辣烫背后的水煮哲学
通常情况下,加热食物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通过火烧火烤把食物弄熟,包括烧烤、铁板烧、炙子烤肉、烤面包、挂炉烤鸭和烤红薯等等,基本都可归为这一大类。
另一种就是通过中间商把食物弄熟,包括油炸和水煮以及蒸制。不管是水,还是油,或者是油水混合物,它们都是通过先加热中间的介质,然后再通过二次传导,把食物煮熟。这一招有着深厚的文明积淀和典型的东方智慧。
在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之后,古老的中国先民们学会了用火烧熟食物。后来,随着黄帝发明了土陶瓦罐,先民们又学会了用水蒸煮食物。从人类获取食物的进程来看,从火食到水煮的演进变迁是一场食物革命,而这场饮食革命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水煮食物显然都是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传承的。
从一点上来说,今天的我们都有一个吃食水煮食物的胃部基因。相对于烤制的食物,水煮的食物不是那么干巴和坚硬,利于柔软的胃部接受和吸收。而且,水煮的食物符合中国的阴阳平衡哲学,火为阳,水为阴,阴阳和合利于人体阴阳和谐。 
麻辣水煮鱼。摄影/生活多美好,来源/图虫创意
当麻辣烫一股脑儿地将所有食物混在一起煮制的时候,又暗合了中国传统的“五味调和”理论,酸、甘、苦、辛、咸,每一种滋味都渗入其中,加上各种食材留在锅里的余香,诸般滋味混合,就形成了一曲味道的大合唱。所以说,麻辣烫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那都是有一定的哲学道理的,这是它被广泛接受的基础所在。 
麻辣烫食材。摄影/城森创意,来源/图虫创意
麻辣烫关东煮这样的吃食之所以能在今天广大的年轻一族中传播流行,还在于它更蕴含着平等的价值观。
一方面,在这一口锅里,所有的食材都是平等的,大家都雨露均沾,底料共享,不分彼此,没有贵贱,更没有上下级的等级观念,不会给食客造成心理上的压迫感。另一方面,对于吃食者来说,它不需要煞有介事地正襟危坐。反正,一人一份,咋吃都行,即使吃相难看点,甚至把油渍溅到衣服上,也都不会影响大快朵颐的心情。
故此,从麻辣烫的本质上,它充分体现了尊重平等,尊重人性的大众哲学。所以,它能被广泛接受,显然符合现代都市人群的社会语法和心理诉求。 
乐山麻辣烫。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段
同时,麻辣烫又是对传统奢华大餐和正餐的一次颠覆性解构。
当下的大餐,都显得过于正经了,在形式和仪式上的过分讲究无形中束缚和伤害了食客们,尤其是刺激伤害了年轻一族食客们的自在感。无疑,麻辣烫是对传统式正餐的一次叛离式解构。你说它是菜吧,它混乱而潦草的相貌全面颠覆了对正统菜肴的人设;你说它不是菜吧,它品种丰富、花样繁多,有滋有味,在一个碗里可以吃到万千菜品的世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碗的吃食还是由自己任性做主。
总之,这个神奇的麻辣烫,它起始于江湖水岸,又以江湖的手法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美食江湖,这也是它们得以流行的另一个社会学基础。 
大家共同品味麻辣烫。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段
倘若有哪一天,你坐在航班上,当一个空中小姐给你端上来一份麻辣烫、串串香或者钵钵鸡、关东煮时,你千万不要感到惊诧,那指定是它们从烟火的人间跑到了天上。
麻辣烫,是吃食的江湖,又何尝不是人世的江湖?
|